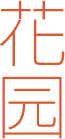作品:寂静之声
一
当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泥泞和风雨中忍受冷落排挤时,他不禁回想起童年在昆西乡下祖父的老宅子里,倔强地不肯去上学的经历。
那是个夏日清晨,初升太阳的明亮光芒,预示着一个灿烂的好日子,松树清冽的芬芳和蕨类植物阴凉的气味飘进窗户,还有园丁新翻土壤的味道,以及渐渐成熟的桃子的甜香。但这一切,并不能让小亨利心情愉悦起来。
他记得自己站在楼梯口,紧握拳头,施展一个七岁孩子所有的辩论技巧和反抗策略,情绪激动地抵制“上学”这一“对儿童而言恶劣之极的行为”。
大人们被他突发的执拗弄糊涂了,保姆、姐姐、母亲甚至祖母,纷纷败下阵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亨利始终坚守自己的小小“阵地”,不肯离开半步,就像一个骄傲的勇士。
他们制造出那么大的声响,最后,楼梯上的那扇门打开了。
在昆西老宅,这扇门后的房间被叫做“总统书房”,曾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家里的办公室,此时属于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的祖父,他也曾是美国总统。
亨利和祖父关系很好。老人的衣橱里倒扣着一排排雕花玻璃杯,里面“关押”着各种虫子,有的是尸体,有的半死不活。退休的老总统对昆虫学很感兴趣,小亨利就是他忠诚的追随者和“同伙”,帮他在花园里捉虫,又掩护他从厨房里偷来这些玻璃杯,并和他一起英勇地面对祖母的数落。
而此时,祖孙俩的小同盟暂时失效了,华盛顿的消息让祖父心烦意乱,他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孙子的顽劣行为,因为时任总统的詹姆斯·波尔克先生的“顽劣”更让他头痛。——他只是觉得有必要出来解决一下问题。
但在小亨利看来,出现在总统书房门口的祖父,显得威严又孤独,他缓缓走下楼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拿起帽子,牵着亨利的小手,领他走出家门。
一路上,他们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高大的老人,威严、沉默、若有所思、一言不发,被他牵着的小男孩,惊讶又乖顺,坚持了一个早上的“战略”彻底失败,他除了努力跟上祖父的脚步,别无他法。
很多年后,亨利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他没有责备,没有劝诫,没有谆谆教导,更没有利用大人在力气上的优势。从老宅到学校,他甚至没有说一句话,因此我感受不到他的任何情绪,没有怒气,没有焦虑,没有强迫的意思,也没有展现任何权威性。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觉得他也许都没怎么意识到正牵着我的手,甚至没怎么意识到我的存在。”
就这样,等小亨利回过神来,他已经坐在教室里,目送祖父的身影从学校门口消失。
从那一天开始,这世间所有孩子和学校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与“战争”, 在亨利的生命中奇妙地划上了休止符。
他不再抗拒上课,也不在学校里捣蛋,尽管仍对被教授的内容抱以轻蔑态度——太聪明的孩子通常如此。但他确确实实从“学习”这件事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以至于后来家人们头痛的是如何把他从书本中拽出来,让他到真实的生活中去。
二
当普法战争期间,亨利·亚当斯躲进什罗普郡的温洛克修道院时,他不禁回想起年轻时在伦敦的泥泞和风雨中忍受冷落排挤的日子。
那时他的父亲弗朗西斯·亚当斯被任命为驻英国公使,而他作为父亲的私人秘书,跟随父母出使英国。
所有人都知道那不会是轻松的出使,南方叛军政府正积极争取唐宁街的支持,而英国也将之视为分裂合众国的好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政府对这次出使寄予厚望,毕竟亚当斯家族有和唐宁街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弗朗西斯的父亲——第七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曾说:“对于英国人头脑中难以理解、更难以消除的偏见和愚蠢,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说真的,我实在有点厌倦了旷日持久而徒劳无功地教导英国人认清他们自己的利益。”
事态发展比预期还要糟糕,弗朗西斯·亚当斯先生带领的公使团还在路上,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就接见了里士满叛军政府的“公使”,一改英国政府之前的立场,承认了南方联盟的地位。
在亨利后来的人生中,结识了不计其数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但他想不出还有谁能像他父亲一样,面对突如其来的,对其外交生涯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保持冷静,不动声色,没有流露一丝紧张和动摇,也没有说出一个激烈的字眼。
他们在丽晶大街的马里奇酒店住下,没有人来拜访,也没被安排任何接见,整个公使团就好像被英国政界和社交界放逐了一样。作为公使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私人秘书,亨利的处境更是尴尬,他拜访了一些在英国求学时的老朋友,去了一些曾在其中如鱼得水的俱乐部,发现自己所到之处,谈话陷入奇异的沉默,然后转向天气和猎狐犬,仿佛他只能理解这两个话题。
父亲这样对他说:“当整个英国把华盛顿政府看作一团乱麻,把林肯总统视为恶棍的时候,辩护是没有用的,同他们解释分析更是徒劳。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任这种情绪尽情发泄,直到它耗尽精力,开始自我怀疑。——儿子,学习如何保持缄默,比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更困难,但我们必须学会。”
母亲的建议更直接:“挺直腰板,保持微笑,找一些像样的事让自己忙起来,只要你不是无所事事,就不会显得可悲或可笑。”
于是亨利接受了《波士顿邮报》的委托,调查曼彻斯特的棉花市场,写成报告寄回国内。报告非常精彩,客观又详实,《波士顿邮报》全文刊出,大受好评。
随后,《泰晤士报》转发了这份报告,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作者的名字,就对它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尽显英国媒体的机智刻薄。接着它又为社交界贡献了无数抖机灵和施展口才的机会,那些从没看过这份报告,甚至不知它写了什么的人,尽情施展毒舌,奚落嘲笑,还从来不忘捎带上作者。
这让亨利很长时间处在一种几乎是懵懂的惊愕状态,就像一个人遭受了太不可思议的打击,一时间不知道这打击来自何方,所为何事。在这种情形下,他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如父亲所说,不做辩护,不予以解释,“任这种情绪尽情发泄”。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实在太难了。有一次,在波蒂忒·孔茨小姐家的客厅里,客人们的闲聊让他如此难堪,以至于做出了自七岁之后就再没有过的行为:他躲到拐角处的窗帘后面,祈祷没有人发现自己。
在这最难捱的时候,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了,英伦三岛笼罩在哀悼的黑色中,一切都被搁置下来,包括政界的尔虞我诈和社交界的飞短流长。
这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
尽管被看作一个注定倒台的政府中形同虚设的公使,但弗朗西斯·亚当斯先生无懈可击的得体言行,从不制造噪音的高贵态度,使他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好感和接纳。人们开始不把他视为身份可疑的外交官,而是值得结交的真正绅士,一个虽持不同政见,但其意见确有价值的外国顾问。到后来,连女王陛下也把他叫作“我的美国反对派领袖”。
当亲王的丧期结束,天气转暖,伦敦社交界重新恢复活力时,亨利惊讶地发现,公使团有了一些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且都不是泛泛之辈。
战争局势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亨利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星期天的下午,维克斯堡战役的消息传到伦敦。当晚,在一个聚会上,《泰晤士报》一位叫德尼纳的记者,一见到他就发出胜利的欢呼,张开双臂拥抱他,热烈地祝贺他,完全忘了之前他们报纸曾对亨利怎样口诛笔伐。
之后这个年轻人在伦敦度过了愉快的五年,最大的困境无非是社交界的邀请太多,难以取舍平衡。
但他再也不会真正投身其中了,无论是媒体、社交,还是政治,对这世间一切“有用”、“有价值”的事物,他开始抱持一种清醒的怀疑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永远地将“成为有用之才”这一人生负累,从肩头卸下了。
三
多年之后,当亨利·亚当斯独自搬进拉法耶特广场豪华的新居时,他不禁回想起普法战争期间,躲进什罗普郡的温洛克修道院的日子。
那是他时隔九年再次来到伦敦,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却收到意大利卢卡城发来的电报,他的姐姐露意莎从马上摔下,受了重伤。
露意莎比亨利大十岁,婚后定居在意大利,在兄弟姐妹中,亨利最爱她。他曾说:“女人是永远不会将人带入歧途的,会这样做的都是男人。”他这份对女性近于信仰的善意,正是源于和姐姐的亲密关系。
当然,人人都爱露意莎。大家都说她是亚当斯家的孩子里最漂亮的一个。而任何人只要和她相处十分钟,就会完全忽视她的美貌,只因她是如此热情、快乐、充满好奇,生机勃勃又富有同情心——那还是一个能欣赏这些美德胜过容貌的时代。他们的祖母曾说:“露意莎能同时给二十个人出主意,还都是好主意。”
所以亨利到英国求学的第一个假期——事实上还没放假,他就急急忙忙越过英吉利海峡,赶到阿尔卑斯山下的夏莫尼镇,和露意莎会合,姐弟俩沿着据称是欧洲最美的马车道,一路到米兰,再往南方继续游荡。
五月的意大利,仿佛在画卷中或天堂里。如果让亨利列举一生中快乐的日子,那么和姐姐在意大利共度的时光,必定是最闪亮的一段。
在那不勒斯,他们还凭着舅舅西德尼·布鲁克斯的关系,有机会参加了加里波第的晚宴。那天加里波第穿着蓝色法兰绒衬衫,相貌文雅,声音柔和,宁静的外表中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单纯。亨利被他迷住了,他则被露意莎吸引,而露意莎对亨利说,她觉得加里波第身上有一种集爱国者与强盗于一身的气质,典型的意大利英雄的气质,“他是一个勇敢的历史参与者,尽管根本没弄明白游戏规则。”
过去了许多年,亨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的露意莎,穿着红色丝绒长裙,像一团小火焰,几乎能灼痛人的眼睛。
接到她坠马受伤的电报,亨利连夜赶往卢卡城,开始还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露意莎喜欢骑马,从小到大不知从马背上摔下来多少次,每次都有惊无险,这一次似乎也是如此。
她的床边挤满了亲友,更多的人从各地络绎不绝赶来。窗外是托斯卡纳永远艳阳高照的蓝天,亚平宁漫山遍野的葡萄园。正是葡萄旺盛生长的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甜香,就像是仲夏沸腾的血液,简直熏得人发昏。整个别墅洋溢着这种有点发昏的欢快又甜美的气氛,到处都是鲜花、水果、佳肴、甜品、葡萄酒和音乐,仿佛漫长而盛大的派对,或某个节日。
在这样灿烂的意大利夏日,亨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的姐姐感染了破伤风。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露意莎仍竭尽全力,以快乐、勇敢而不失幽默的态度面对死亡,想要将这欢愉的聚会一直继续下去。
但聚会终究被拖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死亡缓慢而确定无疑地侵蚀着她,肌肉僵硬,全身抽搐,如同被拷问一样绷紧肢体;欢乐的气氛一点点剥落,痛苦一寸寸地夺取领地,冷酷而坚决。亨利已不再年轻,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但他仍觉得这世界的一重舞台背景,在他面前轰然坍塌,露出了无常、无情而无秩序的本来面目。
露意莎的葬礼后,全家人都觉得她丈夫只怕要殉情,于是陪着他离开卢卡,到阿尔卑斯山间度假,还有几个朋友同行。亨利显得颇为镇定,就算来到当年与露意莎同游之地让他心碎,这心碎也未被任何人看出。
勃朗峰上的积雪依然反射着阳光,仿佛天国的光环;山坡上的草地依然青葱,开满了矢车菊、三色堇和雪绒花;依然游人如织,暖风吹动少女的裙裾和缎带,把孩子们的欢笑声送出老远……但在亨利眼里,这些都只是世界在人的感官里披上的虚幻外衣,就像人们往死者的脸庞敷上脂粉,覆以轻纱。
就在他觉得事情已经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
那时他们在巴黎,歌剧院的演出停下来,从演员到观众齐齐起身高歌《马赛曲》,歌声荡气回肠,再迟钝的人也会为那种力量与精神而感动,亨利在邻座的怒视下也只得起身参与。第二天,他不顾家人和朋友,像亡命之徒一样逃离欧洲大陆,来到英国。
亚当斯家多年的老朋友米尔恩·加斯科尔议员在什罗普郡拥有大片土地,包括一座十五世纪的修道院,里面有些建筑还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尽管经过翻修,修道院住起来仍算不上舒服,唯一的优点是极其安宁,除了日落时分归巢的群鸦,再没有任何声响来打扰几乎是亘古的寂静。
这份寂静正是亨利希冀和渴望的,整个八月,他躲在修道院,宁静在这里仿佛成了有形之物,笼罩在视线所及的万物之上。这是他自幼就熟悉的老朋友,比一切亲情、友谊、尘世的欢乐更能进入他灵魂深处,就像是轻柔的雾霭或纯粹的气息。从他还是个孩子起,每当他的世界出现裂痕,他的生活陷入困境,或是灵魂面对可怕的考验时,最终都是这样的沉默与宁静,平复了一切,使披在真相之上虚幻的外衣具有了实质,能够至少是暂时地将酷烈与冰冷抵挡在外。
在八月的英格兰乡间,古老的修道院深处,亨利·亚当斯终于真正认清了自己,与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所处的社会,连同这社会所在的世界,达成了某种共识。
“这不是灵魂与世界无情的斗争,不是灵魂与人类罪恶的抗衡,精神和灵魂真正的对立面是‘耗散’,它有各种表现方式,社会生活、爱、亲情、友谊、崇高的目标、责任、荣誉……永远地诱惑人生活在外部声音之中,生活在羁绊和共享之中。但孤独是精神进步的必要条件,正如在静默中学会无知,才是获得真知的必经之路。
“对于灵魂与‘耗散’之间永恒的角逐,有两种解决之道:沙漠,或是双重人生。一个人可以从社会生活中完全隐退,一个人也可以不止在一个世界中生活。前者更纯洁,但有陷入谵妄的危险;后者更慈悲,但有走进虚伪的危险。可是如果一个人不这样做,他的灵魂与精神就会在耗散中分解、散开,化为虚无;如果没有人这样做,世间一切最终都会陷入混沌和无序的旋涡。”
在那个宁静的八月,死者在泥土下长眠,战火在海的那一边燃烧,亨利·亚当斯一度走到了沙漠边缘,最终却还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回到他所属的世界,但又永远地与之分离开,永远在另一个世界里拥有了另一重生命。
“我选择站在自然与历史一边,与人的激情和利益对抗——用最安静的方式对抗,做一个诚实的观察者,一件工具,就像是一只气压表、一台计步器,或是一个辐射计。”
四
当年迈的亨利·亚当斯,坐在洛克溪公墓那座著名的青铜雕像下,凝视着雕像沉静的面容时,所有与妻子共度的时光,如水一般静静淌过。
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午后,他的妻子玛丽安·克鲁瓦·亚当斯服下大量鸦片酊,结束了生命。
那时他们在华盛顿拉法耶特广场的新居刚刚建成,还未入住。这座宅邸由亨利·哈勃生·理查德森设计,挨着国务卿助理约翰·海伊的宅子,他是亨利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妻子和玛丽安也是好友,他们都对未来比邻而居的生活满怀期待。
但是玛丽安没有住进新居,她选择了死亡。
哀悼与同情如潮水般涌向亨利,但更汹涌的是质疑与猜测的声音,他再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先是《太阳报》、《晚间邮报》这样的八卦小报,然后是他熟悉和曾经撰稿的《波士顿邮报》、《纽约先驱报》、《论坛报》、《纽约国家报》这样可敬的媒体,最后连《新耶路撒冷报》和《北美论坛》之类也加入进来……时代在进步,一个卷进敏感事件里的公众人物不再只是媒体和社交界的猎物,更多的民众也参与到这样的狩猎中来,手法也更为丰富多样:信件从邮箱里漫出来,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院子里,送电报的人络绎不绝,花束从围栏一直摆到前廊,还有人朝他的房子和马车扔石头;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在路上拦住他,在餐厅和俱乐部里围着他,在车站和咖啡馆里盯着他看;有人拍他的胳膊和肩膀,以示支持,有人把玛丽安的照片举到他面前,把他叫作凶手;还有人给警察局寄去各种证据,证明他的清白或有罪,又有人呼吁国会为此举行听证会……即使在欧洲大陆,人们也总能认出他来,指指点点,神情或是同情,或是鄙夷,或是暧昧的心照不宣。
对所有这些,亨利·亚当斯一律回以沉默,一言不发。
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人,说一个字。
只有一次,他把奥古斯塔·圣高丹的一座青铜雕像,安放在洛克溪公墓玛丽安的坟前——它原本是雕塑家为他们的新居制作的。亨利对约翰·海伊说:“一条虫所能做的最有尊严的事情,就是坐起来,安安静静地坐着。”
他独自搬进拉法耶特广场的宅邸,在那里住了三十三年,读书、写作、漫游、招待朋友、与家人相聚……他渐渐老去,朋友和家人一一离开人世,又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时间流逝,人们开始再一次向他身边聚集,来自各个国家的政客、学者、精英和时尚名流……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正在一战期间,家中仍时时高朋满座,仿佛成为华盛顿一个时代标志,标志着风雅、睿智与正直的老时光。
但是,有些事,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始终缄口不言。
玛丽安墓前的青铜雕像也成为洛克溪公墓的一处景观,很多人专程去看它。而这雕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据传是雕塑家本人透露,亨利·亚当斯先生找他的时候,要求的作品是一尊佛陀。
然而这座雕像并不特别像佛陀,甚至没有明显的东方特色,只是一个人安详地坐在那里,长长的垂地的头巾下,是一张沉静的脸,闭着眼睛,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关于这座雕像,亨利·亚当斯也从未说过一个字。只是偶尔,通常是春季,于清晨或黄昏,他避开人群独自前来,在玛丽安的墓前坐下,仰起头,看着那在时间的侵蚀下,在光影变化中,始终沉静安详的面容。
五
当年幼的亨利·亚当斯被祖父牵着小手,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努力跟上祖父的步子,又偶尔抬起头,偷偷打量老人在阳光下沉静的侧脸时,他并不知道,很久之后,在洛克溪公墓一座雕像下,年迈的自己,仰起头来,在雕像那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青铜面容上,看到的是同样的沉静的光芒。
我到了那棵神圣的菩提树下,乔达摩涅槃的树下。如果他们给我的解释没有错的话,那么与这个世界脱钩,即为涅槃。
然而,总有一两点尘世的羁绊,横亘在最后一跃之前,甚至在佛最神圣的树下,我想到你的时候,也比想到祂的时候更多。
——亨利·亚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