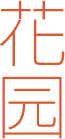作品:雪夜松谭
前面说到何老爷一干人风雪渡口偶然相聚,围炉夜坐,只将闲话来消磨时光。却是老掌柜先问何老爷和石翁:“敢问二位可认得兵部员外郎李公又玠,别号怡亭先生的?”石翁思忖片刻:“老朽在京师时,却未曾听说。”何老爷沉吟:“仿佛有此人,名字可是李卫?”那小厮便道:“老爷记得不错,这位李爷方升了户部郎中。”
夏老掌柜听闻,点头说:“原来如此,小老儿当时便知他是有造化的,将来必定不凡。好叫各位得知,这位李公是丰县人,家境甚饶,两年前捐了员外郎,渡江北上时便是在小店落脚,就住在前面过来第二间。只他来的那日颇有些古怪,天气本极好,江中船只往来不绝,到午后忽起了大风,小老儿在渡口几十年了,那般大风却也未曾得见。当时李公所乘之船正在江心,大伙儿出来看时,都说‘了不得了’,料这船必定倾覆,船上之人绝无生理。有那知晓家人在船上的,已纷纷到岸边哭将起来。”
说到这里,郑生“啊哟”一声,说:“我记得了,那日我家隔壁婆子正在船上,她儿子在我家修灶,扔下刮刀就往江边跑,边跑边哭。”阿珠便也忆起那一日的大风,“且是来得突然,都说有人往江里倒了狗血,龙王爷发怒了。”
夏老掌柜道:“这却是胡说了。然则那风实在来得突然,止得却更是离奇,顷刻之间,风平浪静,将将那船进得码头,天色便又黑了,狂风暴雨随至,比方才还更骇人。就见船上众人扶携拉扯着上得岸来,都顾不得躲避,乱哄哄地朝个道士叩头拜谢。那道士也不理他们,昂然自去了。唯有李公,也不顾下人,也不顾行李,追着道士疾走而去。风大雨大,也不知道士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有人眼看着那道士不见了踪影,唯有李公转头回来,失魂落魄地,倒把他家人唬得不轻。
“后来小老儿也是听李公说起,当时众人上船渡江,耽搁了片刻,原来是个江西的客商,为着渡资与船家争吵起来,非说比半年前渡江时贵了几文钱。当时道士恰站在李公身边,见状摇头叹息:‘命在须臾,还计较这几文钱作甚。’
“后来船至江心,大风方起时,这客人正立于帆下,帆脚扫过,一船人恰恰将他扫下江去,哪里还有命在。船上众人连李公都吓得了不得,直道此番休矣。那道士却作起法来,步踏罡斗,念念有词,真就风平浪静,直到渡船靠岸。全船人赖以活命,独独死了那个江西客人。
“那李公是实诚人,追着道士不放,定要重谢救命之恩。道士便对他说:‘方才那人堕江,是他注定命丧于此,我也救他不得。尔等不应死于此时此地,我岂能不救。这是各人命数,谢我作甚?’
“那时李公方捐了员外郎,正是气盛心炽之时,须臾间目睹生死,又听闻此言,不由得把一片功名之心,尽皆灰了,叹道:‘原来如此,多谢道长指点,学生此后终身安于天命,不为奔波钻营之事矣。’
“那道长却又说:‘李先生此言又偏颇了,不为钻营之事可也,不为奔波之事,却做甚么官呢?须知人生一世,于自身穷通际遇,固当看得淡泊些,莫为排挤倾轧之举。想那李林甫、秦桧之流,纵然不构陷忠良、祸乱朝纲,亦能权倾一时,只因他们命中便带着相印。偏又为了弄权,作那些勾当,只是徒增恶业,祸及子孙耳。
“但若是为着国计民生,大局关切之时,则万不可求签问命,甚至莫要权衡利害,只管去做当做之事,行当行之道。要知天地之生人才,朝廷之设官吏,就是为着社稷苍生挽回天命、补救造化。若阁下来日手握重权,遇事束手委命,只说天意如何如何,人力岂能为也。则天地何必孕育人才?朝廷何必设立官位?
“李先生熟读经史,应当知晓,当年先贤仲子宿于石门(——阿珠听到这里,附耳问孙娘子:“仙仙种子是个甚么?”孙娘子悄悄告诉她:“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晨起入城,司阍者问‘大夫何来?’答曰:‘自孔门。’司阍者便说:‘可是那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
“连看门之人,都知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如诸葛武侯《出师表》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这才是真正有抱负、有作为的圣贤大能于‘天命’的态度。李公李公!你可要记住啊。’
“李公不由得汗流浃背,悚然受教。又问道士姓名,道士笑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怕吓着尔等。’
“这是小老儿亲耳听李公说的,李公并不讳言,且拜托小老儿,往来客栈投宿的,但有书生学子,乃至公门中人,但有机会,便将此事说与他们知道,‘使此金玉良言,入天下为官为吏者耳中’,这也是李公说的。”
听罢此事,在座众人相对嗟叹,何老爷且说:“李又玠有此等胸襟,后生可畏也。来日京师相遇,倒是当与浮一大白。”又叹道:“承平日久,朝中因循之风渐长,有此见识者日稀啊。”
石翁便道:“谁说不是呢?老朽在京中时,也曾亲见一桩异事,与此相仿佛。只因涉及朝中大佬,便不说是谁了,各位听听便是。
“那还是老朽在高侍郎府上时,有位清客书生,姓苏名梦仙。一朝晕厥过去,气若游丝,垂垂将死,高侍郎已赏下安葬银子。他却又醒转过来,原来并不是寻常晕厥,却另有一番奇遇。”
阿珠便插嘴道:“这位苏老爷可是晕厥之后,三魂六魄悠悠荡荡,不觉到了地府,亲眼得见阎王爷审鬼囚?”
石翁愕然:“小娘子如何知道?”阿珠吐了吐舌头:“戏文曲子里不都是这么唱得么?”又笑嘻嘻地说:“您老莫恼,回头我给您老唱一段《胡秀才骂阎王》,不要钱的。”夏老掌柜忙呵斥她:“不要多话!”孙娘子也直拽她的袖子,嗔令她莫要做声。
石翁倒不以为忤,笑道:“原来如此,是老朽孤陋寡闻了,来日再向小娘子讨教。却说那苏生果然自陈霎时间诸事不晓,只觉三魂六魄悠悠荡荡,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处,雕梁画栋、殿堂森然,正是十殿阎王第三殿洞明普静真君宋帝大王南涧余公所在,专司犯上作乱、尸位素餐、草菅人命、不辨忠奸者。”
阿珠却又没忍住,拍掌笑道:“老爹好刚口!还好老爹不说书,老爹若说书,我们都没饭吃了。”
夏老掌柜勃然变色,便要呵斥,何老爷那边没掌住笑出声儿来,忙向石翁告罪:“得罪得罪!”石翁也笑了:“哪里哪里,何大人自己说过,我等有缘相逢、围炉夜话,有什么放肆处,都不要计较。”
阿珠上赶着为石翁斟酒,连称“死罪”,石翁见她笑靥如花,哪里还顾得计较,接杯时偷偷往她手上摸了一把,被阿珠横了一眼,越发酥了半边。还是郑生咳嗽一声,他才端正神色,继续说道:“那苏生素来有胆气,心知此乃第三殿黑纯大地狱,却也不甚恐慌,既来之,则安之,且领略一番地府风味再说。
“就见一个穿着官服的鬼魂上得殿来,红宝顶戴、仙鹤补子,气派俨然,昂首道:‘某一生清廉,所到之处,‘但饮江南一杯水’,再无半分扰民之举。’
“阎王爷听闻,冷笑一声:‘朝廷设官吏,就是为了治理四方,上至宰相,下至小吏,各有职司。若不要钱就是好官,何不放个木偶石雕在衙门里,连‘一杯水’都不饮,岂非比大人还要清廉?’
“那大员愕然,半晌方说:‘某一生为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纵然无功,至少无过。’
“阎王怒道:‘你一生只求自保,甚么人也不愿得罪。当年某案某案,你明知另有内情,为避嫌疑而不说,你对得起涉案蒙冤的子民么?!某事某事,你明知于国于民有利,只是怕麻烦,就避而不提,你对得起功名俸禄么?!你以为朝廷为何三年一考绩?慢说人间朝廷,我这地府诸般职司,哪个敢这样闲混!休说无功无过!来到我处,当官的无功就是罪过!’
“那大员闻言,脸色惨然……苏生正看得有味,忽听得有人呵斥:‘哪里来的生魂?’苏生一惊,只觉吃人在顶心猛拍了一记,天旋地转间,已回到人间,就不知那大员下场如何了。”
听到这里,旁人倒还罢了,何老爷不觉叹道:“不意圃翁身后,竟有此等传闻,虽说世事自有公论,然而名途宦海,艰险至此,也不由人不悚然啊。”
见触动何老爷心思,石翁便有些讪讪的。这时,何老爷那小厮却说:“这传闻小的也曾听过,且还有后话呢,待我说与各位。且说那大员被阎王爷一番抢白,不由得惶恐起来,踌躇不知何以置手足。那阎王爷这会儿倒放平了声气儿,说:‘大人也莫要沮丧,只因我这殿上规矩从来如此,但凡气盛自得者,便要敲打一番,不然于来生福寿有碍。世间为官为吏者不知凡几,平心而论,如大人这般清廉自持,尚可算得三四等好官,来生犹不失冠带也。’”
众人听闻,不由得都笑起来,郑生道:“竟还有这般找补到阎王殿上的,‘盖棺定论’犹嫌太早啊。”何老爷也笑叹:“只是讽刺天下官吏也太毒了些。”唯有阿珠一脸茫然,悄悄和孙娘子说:“老爷们说的甚么,又笑得甚么,我怎么一些也不懂呢。”
石翁却说:“我看这世间鬼神之说,大抵如此,无非是借阴司故事,发人间不平之气。”又问何老爷:“何大人学究天人,您倒是说说看,这世间真有鬼神之事否?”何老爷连忙谦让:“岂敢岂敢,哪里哪里。”郑生又问:“听闻何大人与泰西诸国之人多有交往,则不知鬼神之说,是惟我大清有之?还是举世皆然?”
何老爷沉思道:“这样一说,倒教我想起雷永维先生来。雷先生乃法兰西国人氏,曾说彼邦有位大儒,天文地理、格致算术,无不精通,才是真正旷古烁今、学究天人者。有人便问这位大儒鬼神之事,大儒答曰,‘吾宁可信其有也。’且分说道:‘倘我辈信其有而实无,无非浪费些香火钱,有何损失耶?倘不信而实有,则大限来时,鬼神座下,将何以自处?两相权衡,吾宁可信其有也。’”
众人都笑:“果然是大儒,看得通透!言之有理!”石翁说:“维考究大儒言下之意,还是知其无而且从有。”郑生却道:“老师,话不是这么说,您可知黄叶先生的身后事?”
石翁闻得此名,先叹息道:“黄叶道人着实可惜了,好一笔丹青哪!”郑生便与众人从头说起:“这位黄叶先生,姓潘名班,沧州人士,自号黄叶道人,工书善画,与先父交情甚笃。听先父说,二人年轻时曾在南通李先生借水园中小住。半夜时分,潘先生听闻有人敲窗,乃一女子隔窗低语,竟是自荐枕席来。潘先生恐生事端,严词拒之,且密告主人。”
听到这里,夏老掌柜点头:“这才是老成之举。”阿珠却撇嘴道:“我却不信。”郑生笑道:“信不信咱们倒也不必细论,只江南故老相传,借水园中确有这么个女子,好有些年头了,不知是甚么花妖狐怪、山精木魅,偶出为怪,终不害人。李先生且私语先父曰:‘潘生只怕此生不得发达了。’原来传闻此女子轻易不出,惟遇注定沦落的有才之士,才肯现身一荐枕席。”
何老爷不由得抚掌:“此怪可爱,真可谓‘风尘慧眼’也!”石翁也笑道:“此事老朽也有所耳闻。只是说来惭愧,老朽也曾借宿园中数回,却是一回也未曾得见。想是才疏学浅,不入佳人法眼。”
众人都笑,郑生说:“何老爷圣眷方隆,老师名动公卿,于‘沦落’二字无干,想是借宿多少回也无缘得见的。倒是学生近年来自觉丹青笔墨略有寸进,沦落更是日甚一日,不由得颇为意动,有心去尝试一番,只是碍于家中河东狮耳。”
说得众人又笑起来,笑罢,郑生道:“然则潘先生果然后来时运不济,听闻流落京师,颇为潦倒,鬻字画勉强糊口。家贫无以娶妻,唯有一妾相随,也不知甚么来历,倒是与先生恩爱非常,菊村先生曾说与先父,直叹为‘陋巷穷屋,神仙眷属’。只可惜没过几年,潘先生偶感风寒,竟过世了。”
石翁叹息:“可痛可惜,如今黄叶道人的遗泽,也颇为世人所宝了。”
郑生道:“时也命也,世间才子际遇,大抵如此。只听闻潘先生临终时,唯挂念爱妾,说:‘吾无家,汝无归,吾一贫如洗,汝必不能守,也不必守。幸汝无父兄掣肘,我无家人拖累,汝可自择良人而嫁。倘汝所嫁得人,吾于泉下亦幸甚。惟每年于吾忌日,焚香一祭,余愿足些。’只因此妾性情柔婉,不通世事,潘先生委实放心不下,便又托付邻家老妪:‘必寻家道殷实、性情忠厚者嫁之。’
“后来老妪果如潘先生所托,为其觅得一殷厚行商。行商家中虽有大妇,却并未将此妾携归,于京城赁宅安置,俗语所谓‘两头大’者。方议嫁时,此妾曾言:‘妾孤身一人,一应聘金彩礼、妆奁陪送,皆不必操办,只有一事,要准我每年于亡夫忌日,到他坟前一拜。’行商爱其颜色,欣然许之,且曰:‘既能不忘前人,则来日必不负我。’
“第二年潘先生忌日,此妾果至坟前祭拜,邻妪相随,亲见其泪落香炉间,轻烟袅袅而起,绕其身数匝,拂面掠鬂,久久不散,若有所依。而后此妾自言每夜合眼便见潘先生来至床前,宛如生时,由是染上心疾,渐渐沉重。适逢行商归乡,邻妪便欲请道士做法驱赶鬼魂,此妾再三不许,至行商归来,已缠绵病榻,奄奄一息。
“行商大惊,闻知前因,也命延请道人术士,此妾伏枕叩首,泣曰:‘蒙君垂怜,万死难报,惟故人情重,知我虽寄残生于世间,日日夜夜、煎心焦首,片刻未曾释怀,因魂魄来依,曰:‘孰料卿如此自苦,我之过也,倘果如此,何不随我于地下。’自知不起,且不以为恨,唯恨负君深恩,无以为报,生生世世结草衔环,报君大恩,望君成全。’
“商人知其心意,乃欲与前夫合葬。叹曰:‘汝心在彼,吾留此躯何用?汝一女子,尚如此念旧重情,吾岂不能为慷慨义举?’许诺归葬前夫,此女便逝去,而商人竟真依言将之与潘先生合葬一处。先父与菊村先生闻之,还曾前去祭拜。那时商人已离京回乡,邻家老妪犹在,为二人言之,相共嗟叹良久。”
石翁惊讶:“老朽也曾去潘先生与小夫人墓前拜祭,只是不知还有这一段故事。”郑生道:“我也是听先父说起,此事当年颇惹物议:有说此女别嫁后感伤而亡,何如当日不嫁而殉。既已琵琶别抱,便负前夫,已嫁而心系故人,是负后夫,可谓进退无据也。也有说潘先生既已许嫁,又魂魄来依,是窥他人妻女,可谓死而悖德。乃至有说此商人不知人伦大防,不能约束闺阁,以失贞妇人博慷慨之名,貌似忠厚,实则大奸。故当事人皆欲隐之,讳莫如深,渐渐不为人知,唯有先父等旧日故交,略有所闻,也都为亡者讳,不欲多谈。今夜与各位相得,谈及鬼神生死之说,偶然想起,诸位皆是仁人君子,还望莫要传扬才是。”
石翁闻言,怒气上面:“是何言哉!用情之深至此,遭际之痛至此,彼辈是何心肝!乃以凛然大义,苛责一贫困交加、不识诗书之寻常女子!使此至性至情之事,至义至厚之举,不得传于世间!真真岂有此理!”何老爷亦叹:“石翁此言虽偏激,却有道理。《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感其情、悯其志可也,何必苛责之。”夏老掌柜也摇头道:“不是当事人,无言当时事。与旁人甚么相干,积些口德不好么?”
却见那孙娘子听了郑生所言故事,自低头沉思,又听得三人议论,不由得眉头蹙起,口角微动,一抹潮红自腮边直沁到眼角,阿珠看得分明,两滴热泪就在她眼眶里滴溜溜地打转,她却又搭赸着抬手理了理鬓角,借机用袖子把眼泪沾干,站起身来,敛容正色向座上道:“小妇人替天下女子谢过各位老爷了。小妇人只道妇人苦楚,世间再没有男子体会得,却原来也有知书识礼、通情达理的正人君子,能作仗义之言。”说罢拉着两只袖子,端端正正地拜了下去。倒把一干老少爷们,唬得起身避让不迭。夏老掌柜且一叠声地喊阿珠:“我等不方便,你快把孙娘子扶住了,莫教行此大礼呀。”
孙娘子道:“诸位老爷,实是小妇人自家经历,一向耿耿于怀,从未对人说起,事涉幽冥,别有隐情。还望列位听我一言。”夏老掌柜不由得心中暗暗称奇,原来这孙娘子是个寡妇,十数年前迁来此处,无儿无女,上头公婆犹在,皆年高体弱,还有一个瞎眼的太婆婆,全靠她趁钱养家,服侍着养老送终。虽为了生计少不得抛头露面,但为人极是正气,又极是和气。早几年也曾有人与她说媒,知她要供养公婆,便许与她一道扶养老人。孙娘子婉拒道:“男子性情不定,既非亲生自养,难保日后不生龃龉,倘使家宅不安,于人无益,我心何忍。只尽我力气,奉养公婆天年便罢了,改嫁之事,再休提起。”
到三位老人先后亡故,孙娘子年纪也大了,竟是立志要守下去的样子。四乡邻里,谁不感佩,前数年便有人提议为她上表请旌,不料孙娘子极力推辞,坦言:“小妇人是再醮之身,岂敢妄窃殊荣。”把众人皆惊到了,一时间议论纷纷。孙娘子却咬紧牙关,不管他人作何议论,只自摒牢门户,自食其力,兼着怜老惜贫,扶弱济困,天长日久,大家偶尔说起,嗟叹之余,再无人非议。更有如夏老掌柜一般,但有生意,格外看顾她一些。故而此番听她骤然说起身世,别人犹还罢了,夏老掌柜和阿珠不由得格外留神起来。
那孙娘子便说:“小妇人自幼在某府当差,故主恩重,不便透露姓氏,还请见谅。只是小妇人福薄,服侍的小姐出阁前一病不起,夫人伤心,将小妇人胡乱指给个下人打发了,便是小妇人的前夫。虽说夫妻一场,不当说他的不是,然此人实是不堪,纵酒好赌、逞凶横暴,不出几年便被赶出府去,小妇人也只得和他一道流落市井。
“前夫不事生计,仍只顾饮酒赌钱,欺凌邻里,小妇人数回欲与他和离,只是拳打脚踢,再不肯许。小妇人只道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几番欲寻短见,终究年轻惜命,苟且偷生而已。不料有一夜,他自家烂醉后,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非是小妇人淫贱,实在不甘替此人守节,一出孝便嫁了后来的丈夫。
“后夫虽出身市井,又操贱业,然为人忠厚体贴,从不以再醮视我,公婆也待我极好,就和自家女孩儿一般。纵然数年后,丈夫亡故,旁人皆言小妇人命硬,一连克死两个丈夫,公婆也只说自家儿子没福气,从未有一句尖酸刻薄话。那时我便立誓,尽我全力供养公婆并太婆婆,使其饱暖安乐终身,并为亡夫守节,义不再适。
“却不料这时,我那前一个死鬼开始作起祟来,每夜小妇人合眼便见他站在床前,周身湿漉漉地,只盯着我发狠道:‘你既能为他守,为甚么不为我守!倒教我做了鬼还吃同类耻笑,我定不饶你。’如是三五十夜,夜夜摔砖掷瓦、兴风作浪,闹得阖家不宁,且是担忧他有妨公婆康健。而小妇人丈夫新丧,哪有余钱请道士做法禳灾,只得夜夜与他捱着。
“一夜小妇人再忍不住,从床头跳起,与他对质说理,自嫁他之日说起,桩桩件件,尽是伤心毁情之事,数载之间,势同水火,哪有半分夫妇恩义。又说自嫁给后夫,才知世间做人妻子的,还有这样一等境界,情深义重,珍惜体贴;又才知奉养老人家的,还有这样一重回报,嘘寒问暖、知疼知热。我不替这样有情有义的丈夫守着,不供养这般慈祥温厚的公婆,难道要为你这狠心短命,无情无义之人耗费青春么?休说你今日作鬼来找我,你便是请来十殿阎罗,漫天神佛,我也还是那句话:哪怕你抬出十座贞洁牌坊,许来世怎样泼天的福报,我也不会替你守一天!哪怕你说我是再醮之身,守一辈子也是一场空,到头来还得下地狱,来世变畜生,我也要替他守着!你若不信,只管睁大你的鬼眼看着!好的话,我便仍念夫妻一场,每年还有些许冷饭纸钱供奉;不好的话,大不了我毁容剪发,奉养公婆归西后,便到地下,也化身厉鬼与你对质!大家拼个鱼死网破便罢!
“那死鬼最是欺软怕硬,色厉内荏,吃我一通发作,竟自化作黑烟,悄然散去。之后十几年未曾再来作祟生事儿。
“所以要说世间鬼神之事,小妇人亲身经历过,那必定是有的。若说抱憾,唯憾所遇之鬼竟是前夫,而后夫亡故十余年,连梦中都不曾现身,未免伤感。然转念一想,亡夫为人忠厚正直,一生清苦操劳,设若无须牵挂父母,必不致久滞幽冥,想已投胎转世到好人家里去了。心念至此,则唯愿他下一世平安喜乐,纵我永沉地狱,生生世世再不得相见,心里也是欢喜的。”
听到这里,别人犹可,那阿珠早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去扯孙娘子的袖子:“我的大娘,你可心疼死我了!拿着你这样一个好心人儿,老天怎么也不可怜可怜,叫你受这个苦哟!”倒还是孙娘子把她搂住,轻轻拍了两下,自家面上并无更多戚容,仍微微带点笑意。那夏老掌柜便劝阿珠:“你莫要如此,老爷们在此,甚么看相。”阿珠就拿那鹅黄绣花手巾子来擦眼角,擦了两把,又舍不得,依旧掖回去,使手背用力抹了几下眼睛,说:“您老不知道,我就剩了心里过不去,实在说不出甚么来。”
何老爷便叹道:“法不外人情,幽明一理也,圣人尚不以春秋大义苛责世间儿女。何况娘子奉养公婆至孝,不肯行欺世盗名之举,只这两条,地狱必不为汝辈而设。今生已矣,来世或别有造化,也未可知。”石翁也说:“孙娘子莫要感伤,絮果兰因,未为无由,或此念一生,便是来世因缘的根基。”郑生也笑道:“正是。学生说句不当说的,设使学生为阎罗王,遇到娘子这桩公案,定然大笔一挥,判与后夫三生三世为夫妻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阿珠还说:“三生三世哪儿够,须要生生世世才是。”
郑娘子闻言,泪盈于睫,却又喜动颜色,环拜众人:“列位老爷都是君子人,知书达理,一言重如千金,得列位这些话儿,小妇人死而无憾了。”说罢,高高擎起酒壶,为在座众人一一满斟,众人感孙娘子盛情,皆一饮而尽。连阿珠也背过身去,半蹲着与孙娘子互让了一杯。
石翁便说:“人情老易悲。天气既已萧杀如此,更深露重,大家莫要再讲伤情之事,老朽年纪大了,每闻断肠之语,往往感同身受。听不得了也。”阿珠笑道:“那我给您老讲个笑话可好。”众人都说:“最好。”
阿珠便看着夏老掌柜抿嘴儿道:“您老可曾听闻去年夏天,对岸罗家的笑话儿。”夏老掌柜笑道:“你这小贫嘴儿,不知又要编排人家哪一桩。”阿珠撇嘴道:“本来么,他家那小罗掌柜接手后,最是刻薄不近人情。大家都说他家后跨院西楼上头,住进了一大家子红大仙儿呢。”郑生便向何老爷和石翁解释:“鄙乡把修成的狐仙叫作红大仙儿。”小厮笑道:“倒是与京城一样儿叫法。”
阿珠说:“小罗掌柜从不肯认,撑着人红大仙儿是规矩人家,自恃身份、安分度日。”说到这里,众人就笑起来:“好个规矩人家。”阿珠犹正色点头道:“可不是么,那红大仙儿便合人一样,有那不良善的人家,便也有那规矩好人家,只偶然弄出些微声响,等闲不肯现身。便有不知底细的客人住了,他家还合干净客房一般收钱。”夏老掌柜便说:“这却不太合适了。”阿珠道:“可不是。所以去年夏天,有个晚上,那楼上就忽然闹起来,闹了个沸反盈天,整间客栈都惊动了,连四邻八舍都跑到他家后跨院儿里来看热闹。大家都问小罗掌柜:‘你不是说这楼上干干净净太太平平吗?这却是谁在闹?’小罗掌柜无言以答,竟也还忝着脸和大伙儿一起看热闹。
“就听见楼上有男子的声音,泼天喊冤,又有女子的骂声,夹杂着翻滚摔打声,大伙儿都说:‘了不得,这是动了家法罢。’听了一会儿,似乎是男大仙儿在外头养了个小的,叫女大仙儿逮了个正着。就有后头辘轳巷里那户姓刘的秀才——郑先生和夏老听说过他家罢?刘秀才家的娘子好生厉害,听闻给刘秀才写的家法有几十页纸呢。连他家娘子责罚下人时,刘秀才若是说情乞免,都有个罪名儿,按‘属员请托上司’例,要吃二十板子呢。”
听到这里,众人都笑:“这个罪名定得当!”郑生且说:“多谢提醒,我须小心了,切莫使拙荆识得刘娘子。”众人越笑,阿珠越正色道:“那刘秀才日前不知犯了哪条,被刘娘子在脸上抓出几道血印子,想是久惯牢成,不以为意,依旧挤进人群里,一般仰头看热闹,还说:‘啊呀,打的时候莫要跑呀,你让她把气儿打顺了就是,难道还跑得过去不成?’
“正说着,楼上那男大仙儿被打得熬不过了,哭着冲楼下嚷嚷:‘列位邻里都是晓事儿的正人君子,列位客官都是见多识广的壮士,倒是与我说说理儿,世间岂有妇人这般毒打丈夫的!’
“说话间,楼上灯光正明晃晃儿照着刘秀才的脸子,那脸上明晃晃几道新鲜热辣的血印子。众人一齐大笑,都说:‘这事儿在我们人世间也是司空见惯,大仙儿且莫悲伤,看看刘秀才,便知自家娘子还是温柔和气的。’
“那被打的想也久闻刘秀才家风,听得此言,便收起哭声,赶着喊‘刘兄’,只说:‘刘兄,我好苦也。’刘秀才这才不疾不徐地说:‘不苦不苦,我家规矩,尊驾这情形,须按‘谋反已成’处置,岂是几下棍棒能结案的。尊夫人极是温柔大度,尊驾须铭感五内、低头虚心领罚才是。’”
听到这里,石翁一口酒喷出来,呛得咳嗽连连;郑生连忙与他抚背,一边自己也笑出眼泪来;何老爷笑得直掀胡子;那小厮本在与他倒茶,泼出好些,一边甩手呼痛,一边仍笑得停不下来;就连孙娘子,正吹着一把花生,不防花生撒了一地,低头掩口,笑个不休;那夏老掌柜一面笑得直拍胸口,一面指着阿珠道:“好促狭鬼儿,这是人们编排刘秀才和小罗掌柜的,偏你传得绘影绘形儿,就跟亲眼见着一般。”阿珠撇了撇嘴:“我虽未亲见,那晚多少眼睛看着,岂能是编排?再说了,就算是编排,怎么不见大家伙儿编排您老人家和咱们客栈呢?总还是他们自己可笑,而后才有这些神辱鬼戏的事儿。”
说话间,一道白光打帘子缝儿里溜进来,晃晃悠悠地,拨过马褥子的排穗儿,攀上铜火盆的老木架子,和着火盆里的红灰一闪一闪地,跳过铁篦子投下的影格子,一径落入一口羊肉锅子里,照得半凝的羊油闪闪发亮。夏老掌柜看到,说:“啊哟,雪停了,出月亮了。”抬手推开棉帘子,果然好一轮冰鉴银盘般的满月,早升上中天,正渐渐西沉,犹把清凌凌的月光落在雪地上,就如碧海青天,而这一角松棚儿,便作了海中的一叶扁舟一般。何老爷笑道:“如此明儿该有船了吧。”夏老掌柜说:“一准是好天儿,能开船了。”石翁却说:“还好雪景犹能赏鉴一两日,够画一幅小山水了。”何老爷拱手道:“必定是幅好画儿。”郑生笑道:“老师画甚么山水,要我说,画幅雪夜围炉闲话图不好么?”众人都笑,就听见阿珠脆生生地问:“怎么着?那我们也能入了您老的画儿不成?”
微风拂过,棚顶一角松枝上的积雪,不知是被笑声还是风脚惊动了,扑簌簌地落了下来。